
人物简介
高建群,新时期重要的西部小说家,国家一级作家、陕西省文联副主席、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,国务院跨世纪三五人才。高建群被誉为浪漫派文学“最后的骑士”。他的《最后一个匈奴》与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、贾平凹《废都》等陕西作家的作品引发了“陕军东征”现象,震动了中国文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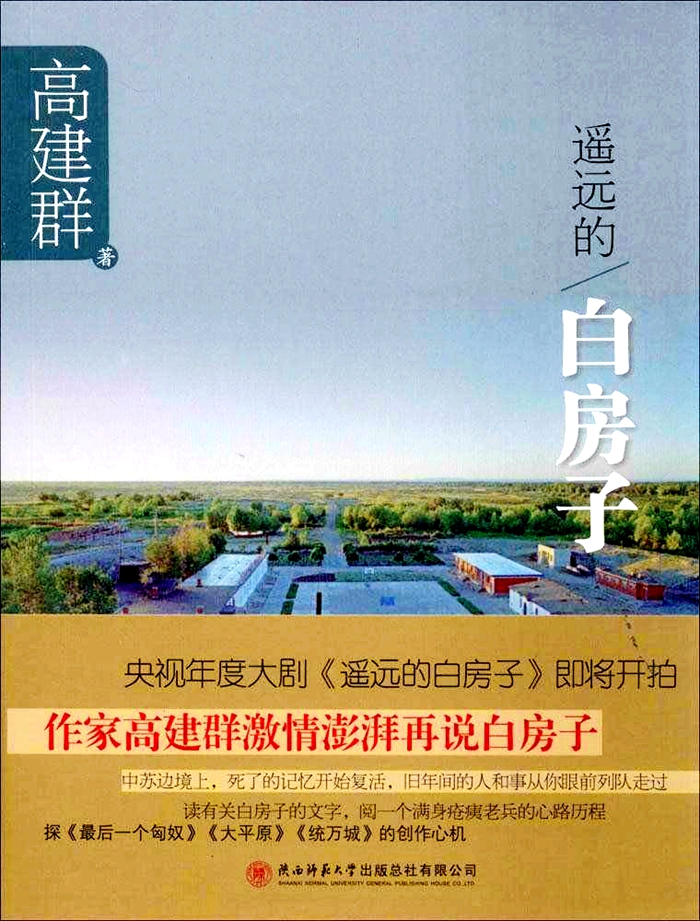
文艺评论
著名作家高建群的中篇小说《遥远的白房子》(载《中国作家》一九八七年第五期),以民间传说为题材,在当代意识的观照下,为我们描叙了一个生动感人的故事,作品在对几个人物的刻划上,回族强人马镰刀的形象塑造最为鲜明瞩目而动人心魄。
马镰刀作为白房子边防站站长,虽职位不高,而担负的责任重大。这位从小当过走私犯,尔后成为绿林头目的人,多年过的是东跑西奔的动荡生活,骤然固定生活在小小白房子的氛围里,这茫茫荒原望不见人烟之地,只显得单调和枯燥,人生应有的欢乐和享受,他是无缘获得的,因此造成他精神和心理上的孤独和空虚。身边虽有哈萨克血统的妻子萨丽哈的陪伴,因民族习俗的相异,她那同兵士们寻情求欢的放荡行为,同他受过回族礼仪的教养格格不入,他恨她而又无可奈何,这气愤和忧郁,更增添了他内心的孤独。他手下的十九名兵士何尝不感到生活的孤寂呢?他们对萨丽哈的接近和挑逗,他生气而又不去责怪,正是他对兵士们的心情的理解,为了稳定军心、镇守边陲这一重要任务,他只好忍辱负重。
卡西尔认为,动物或人,不仅仅是要能适应环境,重要的是能符合环境的要求。马镰刀的文化心理固然使他不能做到符合环境,然而他的丰富社会经历培植下的江湖义气,使他能抑制着矛盾而痛楚的心境,做到入乡随俗。
正是马镰刀这种心理上的孤独感,强化着他的“人是离不开人的”精神上的需求,人类的群体意识搅动着他的心灵,使他对人群有着焦灼的渴慕和向往。
他和十九名兵士组成的巡逻队,只是荒原上一个孤单的小群体,他希冀着多些、再多些的群体出现。机会来临了,两个不同民族的巡逻队在界河边上相遇,由相互的武装戒备到共饮酸奶和歌舞联欢,他和兵士们的寂寞感得到暂时的释 放。民族间的戒备解除了,边防线上应有的纪律和约束淡化了,人类之爱占有了这荒原的空间,两个民族尽情享受着人类生存的欢愉和美好,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的呢? 作家的理想也显然可见。
虽然如此,马镰刀借那“醉卧沙场君莫笑,古来征成几人还?”的诗句,在浇洒他的悲凉的情怀;因为这种人类“联欢”是暂时的,是违禁的。
士官生偷走“借条”,引起两国间边界争端,使马镰刀深感有罪,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道义感;道伯雷尼亚虽因此升迁,但亦深为内疚而忏悔。美好而纯洁的人类之爱被狭隘的民族仇恨所亵渎,终酿成双方边防兵士集体自杀的悲剧。
这一举动,是两个民族间友谊的血的结晶的表露,是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抗议,更是对庄严的人类之爱的维护与升华!当然,人类之爱是以爱国主义为根基的,离开爱国主义而追求人类之爱, 那将是盲目和虚幻。
那遥远的白房子,是圣洁、宁静的象征,是人类相爱的象征。人类是多么希望那洁净的“白房子”不要被人间丑恶所污染,不要被无谓的仇恨溅上械斗的血迹!
那遥远的白房子,如今巍然屹立在中国的土地上,这是历史的承继与延续,中国人民热爱和平,人类希求相爱。

文稿节选
高建群:白房子,一个冬天的童话
1975年的冬天,是一个多雪的冬天。从十月份开始,阿勒泰草原一个礼拜吼一场大雪。雪将戈壁滩严严实实地封住,积雪最深的地方深达两米。巡逻时,一不小心,连人带马就栽到雪坑里去了。位于中苏边界那被牧人称为白房子,军用地图上称作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的地方,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。
一个放晴的中午,前面有兵团斯大林一百号推土机开道,边防站来了一辆吉普军车。车上走下来一位老军人。老军人个头不高,大约有一米六二左右,但是很雄壮,或者用陕西话说很“魁”。他两手总插在上衣口袋里,走起路来迈着标准军人方步。胸膛前挺,一步迈出七十五公分。他和我见过的别的老军人不同的地方是,上衣口袋别着两支笔,一支钢笔,一支圆珠笔。老军人叫那狄,时任新疆军区北疆军区政治部主任。
他是老延安,大约是一九四六年到延安的,是满族东北人。大约做过总政文化部电影局局长。后来因受罗瑞卿案牵连贬到新疆。这次他是到边防一线搞调研。那主任在边防站住下以后,原来的日程两三天后就走,想不到,天空又飘起了鹅毛大雪,因此那主任一行只好住下来,一住就是十五天。我从事文学,或者说,我将自己的一生,与这件被称为“文学”可诅咒的莫名其妙事情捆绑在一起,是因为那主任的这一次行程,或者说因为导致那主任滞留白房子的这一场大雪。
我是1972年12月14日从家乡临潼县何寨公社东高村穿上军装的。16号到西安火车站集中,一群三百多名关中平原上的农家子弟,被装在一列刚拉过马匹的铁闷子火车上,冒着珍宝岛和铁列克提的硝烟,开往中苏中蒙边界。这批陕西兵在乌鲁木齐改乘汽车时,被分为两拨,一拨前往中蒙边界,一拨前往中苏边界。我去的是中苏边界。那路途上所受的折磨,现在想起来还叫人害怕。我途中感冒了,使劲地呕吐,肠肠肚肚好像要吐出来了。一排三十六个人,都坐在一辆卡车上,坐成四排,屁股底下坐着背包。大家面对面坐着,穿着臃肿的皮大衣,脚下毡筒,膝盖与膝盖,严严实实地交错叠在一起。这时我要吐了,眼看就要喷到对面人的脸上去。这时我急中生智,从手上脱了皮手套下来,将它吐在手套里。秽物吐到手套里后,很快结成冰疙瘩。一天坐车下来,到了兵站,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将手套放到火墙上去消冰。冰疙瘩消了,再将秽物倒出来,这手套明天还要继续往里吐。记得路过奎屯,在乌尔禾,在克拉玛依,在布尔津,几乎路途的每一个兵站里,我都做过这样的事情。
这样来到中苏边界,在漆黑的大雪飘飘夜晚,顶着界河对面的照明弹、泄光弹、穿甲弹、信号弹的各种光亮来到白房子。那里大致位置有个喀纳斯湖,大家都知道。那里是我们一连,叫白哈巴边防站,沿着边防线,下来是二连,扎木拉斯边防站,下来就是三连,我的边防站,下来是四连,克孜乌雍克边防站,下来是五连,阿赫吐拜克边防站。
那主任来到边防站时,我已经在这个充满凶险、与世隔绝的边防要塞,当兵快三年了。三年中我写了不少的诗,在纸片上写,在本子上写。大约一种罗曼蒂克的情绪突然钻入我脑子里,促使我写下这些东西。“额尔齐斯河滚滚流向北冰洋,岸边有一座中国边防军的营房”,就是我给边防站办的国庆节墙报上写的诗。那时国内有两家公开刊物,一家是上海的《朝霞》,一家是北京的《解放军文艺》。连队订有《解放军文艺》,只要能找到,我就去看。在这五年中,我只看过一本小说,是前苏联叫《多雪的冬天》的书,是我从开巡逻车的司机的驾驶室里找到的。
《瞭望登记簿》,那上面往往会有“三号口有苏军潜伏哨两名”,“苏松土带一侧有装甲车驶过”等字样。这些填完,再填上“哨兵高建群”。填完《瞭望登记簿》,那枪还在火墙上消着,等到消透,还得一段时间,于是我就着那盏油灯,开始在一个小本上写诗。现在仍记得那天晚上写的那首小诗,诗名叫《给妈妈》。
巡逻队夜驻小小的山冈,
晚霞给他们披一身橘黄。
远方的妈妈,如果你想念儿子,
请踮起脚尖向这里眺望——
那一朵最美最亮的云霞,
是巡逻兵刚刚燃起的火光!
巡逻队行进在黎明的草原,
草原像一只偌大的花篮。
远方的妈妈,如果你想念儿子,
请……
很明显,这个面色黝黑,愁容满面,因为骑马巡逻而磕掉一颗门牙的士兵,是在想家了。遥想渭河畔那个小村子,想他的母亲,想他的年迈的婆和爷。本该他是想用这一段时间来写一封家信报平安的,结果写成一首诗。正当我在巴掌大的小本上埋头写诗时,门开了,走进来两个军人。一个是那副主任,另一个是那主任带来的干事,陕西人,叫侯堪虎,我们叫他“侯干事”。干部查哨、查铺,这是一项传统,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。那主任一行没有睡觉,这时是凌晨一点,查完铺后才去睡觉。
那主任问我在小本上写什么。我说胡乱写,枪还是在火墙上靠着,等着消冰,这段时间就没有事,可以在小本子上胡乱画。
那主任说他要看这个小本,看我在上面写什么。我拼命地用手捂着,把这小本死死按在桌子上,不让他看。我有些害羞,那些最初写作者,当将作品拿出来示人时,大约就像我这满脸窘态。那主任已经伸出手来,抓到了笔记本的边沿,但我仍把本子压得更紧,坚持不让他看。我说,这本写得太潦草,等我明天将它誊写清楚,再给那主任看。谁知他说他是政工干部出身,越潦草的字,他就越能认得。侯干事赶过来给他帮忙,抢走我手中的那个本子。
原来那主任是起了疑心,不知道我在那个小本上写什么。原来那主任此行,是来搞调查的。与白房子毗邻的吉木乃边防站,连续三年跑过去三个士兵。其中有一个河南兵叫尤胜金,在莫斯科郊外的克格勃训练营被训练成特务。后来的两伊战争,有个乔装成阿拉伯人的著名国际特工,名叫“沙漠之狐”,那就是他。1991年,他在偷越我国国境刺探情报时,被我方战士在边境线上击毙。一一但是据最新的说法,他并没有死。前几年新疆开乌洽会,他还来过,身份是俄国商人。是当年边防站的指导员告诉我的。他说有关方面请他去辨认,他隔着玻璃窗,一眼就认出了他。
话说,在白房子暴风雪呼啸的夜晚,三班的营房里,就着这如豆的灯光,双方为写诗的小本争执了好一阵子。争执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。这个懦弱的面色黝黑的小兵,乖乖地将手掌大的笔记本交出来。那主任接过了笔记本,他戴上老花镜,就着灯光开始看起来,越看面色越严峻凝重,呼吸越急促。他大约想不到会是这么一个结局,大约想不到在这样荒凉的、险恶的中苏边界一个小小边防站里,在这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的北部边沿,竟然有一簇文学冲动,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兵在从事写作,或者用大家在说的话说,在“搞文学”。
那主任看完了小本。他过来拥抱我。他的眼睛有些潮湿。他随手将小本交给侯干事,让侯干事用正规的稿纸将这些诗作誊清,然后寄往《解放军文艺》社。他对我说:《解放军文艺》的人我都认识,我原先是他们的领导。诗歌散文组组长叫李瑛,编辑有韩瑞亭,纪鹏,雷抒雁,等等。我写一封推荐信给他们,告诉他们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,告诉我此刻的感受。这就是那个冬天发生的故事。过去了四十余年,却栩栩如同昨日。那主任拿着我的那个小本走了。我开始擦枪,擦完枪以后,上到铺上去睡觉。那是班长睡的头铺。别人早在呼呼大睡,我睡在床上,用两只手抱着两个冰凉膝盖,才慢慢地一会儿睡着了。
几天以后雪停了,那主任一行离开,仍然是兵团斯大林一百号开道,把雪压实,吉普车跟在后面。第二年,也就是1976年八月号的《解放军文艺》上,刊登了我那小本上三首诗,标题叫《组诗:边防线上》,署名是“战士高建群”。里面有《给妈妈》那首,另两首是《装蹄员的心》和《边境线上的小河》。而我接到杂志,已经是十月初的事情了。那年的九月九号,发生了一件大事,就是领袖毛泽东的去世。那天我带领我们班种菜。一个合阳兵,是个马倌,他骑马跑来报告说,赶快回边防站,钻地道,准备打仗,毛主席“老”了。
这样,我们全站人员剃成光头,穿着皮大衣,钻进戈壁滩上原先挖好的水泥工事里。几件换洗的衣服,一点零用钱,包成一个包裹,放进营房的储藏室。包裹上写下了家乡地址和自己的姓名。一旦你阵亡,这包裹将由别人代你寄走。记得给领袖开追悼会的那天,下着大雨。全边防站的人,一个挨一个,顺着地道站了一里多长。一个小发电机在发电,隔一段有一个电灯泡。收音机里播放着哀乐。这时炊事员进来送饭,穿着往下滴水的雨衣,说外面正在下雨。
我接到杂志大约在十月初。人还在地道里。炊事员进来说,兵团的邮递员骑着马,站在围墙外面喊着我名字。我走出地道,翻过沙包子,接过邮递员从绿色邮包里拿出的两捆杂志。除了杂志,还装几沓稿纸和一个《解放军文艺》社的采访本。那两捆杂志不知道经过多少人的手寄到这遥远的边防站,原先的包装全磨光了,路途中又包装过,又用绳子捆过。
这就是我的文学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经过。人们说这叫“处女作”。这个意外发表鼓励了我,或者说蛊惑了我。自那以后,我就一直傻乎乎地热爱文学,从事写作,直到现在。那主任回去后,还给我寄来了一些书。这些书是别人送给他,他又寄给我的,因为上面有作者的题签。这些书有李瑛的《红花满山》、纪鹏的《荔枝园里》、兵团李幼蓉、杨牧、章德益等合出的《军垦战歌》,还有一位维吾尔作家写的长篇《克孜勒山下》。后来我回到地方以后,还将我新发表的作品寄给那主任汇报,并且接到过他的回信。据说,他后来担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、主任,被授予中将军衔。现在他可能大约已经过世,关于他后来的事我是听新疆回来的战友说的。
我是一九七七年的四月十日,离开边防站,坐着大卡车,从额尔齐斯河的冰层上回到哈巴河县城,然后返回家乡的。一九八七年,我写出那部著名的小说《遥远的白房子》,作为我对那段军旅生活的纪念,作为我对领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尊敬的那狄主任的一份回报。
我待过的那个边防站,全称叫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。当地牧民叫它“白房子边防站”,这是满清以及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叫法。边防站辖区内一块55.5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。由于一直由我方控制,所以,在后来中苏、中哈重新勘界、栽桩中,它划归为我方,成为不再争议的中国领土。
那条叫作额尔齐斯河的注入北冰洋的河流,那座横亘在中亚细亚地面的阿尔泰山,那块干草原,那座白房子。它是如此深的楔入我的生命之中,每次想起它都会给我带来一种病态的深深的忧郁。白房子是我的梦魇之乡,我的永远的噩梦,我的十字架。许多年来,我像蜗牛一样背负着我的十字架,走着我的蹒跚的人生。因为它,我才成为现在的我,独特的我。
节选自《从遥远的白房子走来》,《延河》2017年第10期(总第638期)

|